宋史研究中心学者著作介绍(十一)
(转自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1.

《杨辉算书及其经济数学思想研究》吕变庭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6月第1版
内容介绍:从杨辉这个个案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两点启示:第一,筹算数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与国家垄断天文学的发展特点不同,筹算数学与政治环境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就其数学研究和数学教育的特点而言,此期的筹算数学发展具有比较典型的民间性质,因而宋元数学四大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的战乱年代,尽管他们每个人的政治地位较低,人生经历坎坷,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各自在筹算数学领域作出伟大的数学成就,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视野主要地是面向生产和生活实际,如杨辉的数学著作之所以大多都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这些著作能够为人们解决他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数学工具和数学方法;第二,反思“杨辉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从宋元筹算数学发展的巅峰状态到入明朝之后的戛然而止,这个过程不是偶发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以杨辉为例,迄今为止,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杨辉著作中所记载和保留下来的各项数学成就,而较少有人注意分析和考察杨辉著作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问题。如果孤立地看,杨辉著作所保留的数学成就如“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开方法”、“纵横图”等等,确实都是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成就,其意义巨大,不过,只要我们坐下来静静地思量,就不由得会提出下面这个问题:这些科学成就为什么不能继续深入发展并最终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例如,“开方作法本源图”从出现的那一天起,我国基本上就处于“图算”阶段,然而,在欧洲,从“帕斯卡三角形”到牛顿二项式定理,却完成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并很快在组合论、差分法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遂成为欧洲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可见,同是“二项式定理系数表”,理论结果却大不相同。那么,造成这些差距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显然,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仅仅局限于数学本身(即“内史”研究)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宋代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和开放的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宗教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杨辉筹算数学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深刻影响,所以只有将杨辉筹算数学放在当时整个文化巨系统中去加以比较和考察,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杨辉筹算数学除了成功经验之外,它本身所隐藏的致命缺陷在哪里。因此,本书不局限于仅仅阐释杨辉筹算数学的主要科学成就,而是试图从“外史”的角度,以繁荣与危机的辩证关系为视角,紧紧把脉杨辉筹算数学与宋代社会变动、经济转型、理学建构、多级政权鼎立之间的互动关系,着力总结和深刻剖析杨辉筹算数学本身的时代局限,特别是尝试用素描方法来刻画由这种时代局限给中国传统数学发展所造成的那些略显迟钝和僵硬的历史面相。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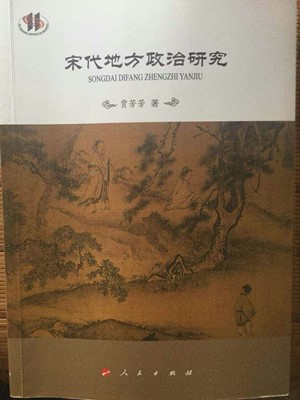

《宋代地方政治研究》贾芳芳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7年9月第1版
王曾瑜 序
这确是一部十年磨一剑的力作,贾芳芳先生前后也不知反复修改了多少次。就我的记忆,个人至少也前后看过其四稿。她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当博士后期间,又蒙刘复生等先生提出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并认真吸取,作了尽可能多的修订和补充,方得于今日面世。此书论述宋代的地方政治,既以贪腐问题的论析为主流,又兼及不少其他相关的方面和问题,无疑是相当系统而深入的开创性专著,在另一个意义,也可说是呕心沥血之作。
贾芳芳先生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毕业后,在新闻界工作多年,接触了不少地方上实际的政情民瘼,不能不使她产生了忧患意识,这是相当可贵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像中华民族那样一个古老的,饱经劫难的,而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既在客观上须要跨越民主、发展和统一三关,三关缺一不可,面临着难得的复兴机遇,又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和积弊,能不忧乎!应当承认,并非是所有的史学专业研究生,都能像贾芳芳先生那样有忧患意识,并且选择了古今相通的研究课题。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1]这是十分深刻的。因为任何一代史家必然会重新研究,甚至改写历史,而其研究或改写的基点无非是当代性。他们必然依据自己对当代史的某些体会,同时也必然按史家个人的人生观,即人生哲学,去重新认识悠远的历史。研究中国地方政治确有其相当大的现实意义,特别在本书的绪论和结语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已作了相当透彻的论析。在此不须重复作者的论述。本书明确论述宋代的地方政治,以贪腐问题的论析为主线,这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活的地方政治制度史的关键所在,也可以说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实例。
翻开中国古代史籍,有关地方政治的各种积弊史不绝书。一方面,朝廷的权力至高无上,要任免或处分一个地方官员,甚至大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另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官的监管,又必然是漏洞百出,地方官玩法侮令、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又有足够的施展拳脚的空间。这就是古人所谓“天高皇帝远”。中国历代地方官场的各种潜规则,或者说是黑道,其实在官场流行了二千余年。细想一下,古今中外的黑社会,其实并非只行黑道,而是行黑、白两道。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地方官自身难道不是穿着官袍的黑社会老大?
中国古代地方上的各种弊政,简直就是在同一个陶范中熔铸而成的,并且积重难返。中国历朝都走不出如此的怪圈。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的总遗传密码,就在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地方上当然也有很少量的清官,但不可能改变十官九贪的大局。《儒林外史》第八回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大约是来自清代的民谚。由此可见,中国历代地方政治,似只能是大同小异,要寻觅重大的、根本性的差别,似无可能。有的先生提出需要研究宋代地方政治的特色的建议,当然也有一定道理。本书在结语中总结的对贪官的“宽柔”之政,大致可算是宋朝地方政治的一点小的特色。
另一更细致的问题,就是宋朝各代地方政治有何阶段性的差别?贾芳芳先生经过努力,感觉难以找出宋朝地方政治的分阶段的演变,就只能量体裁衣了。当然,有的朝代是可以划分些阶段的。例如唐朝贞观之治下,地方政治是较为清明的。但到唐高宗时,武则天重用李义府,卖官盛行,地方政治就变糟了。又如清代,康熙时贪风甚盛,雍正时采取若干措施,贪风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到乾隆时又变本加厉。宋朝的地方政治看来似无如此明显的阶段性,总的说来,是贪风愈演愈烈。如果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认真思考上述总遗传密码,只怕也无法对她予以苛求了。
宋代地方政治以贪腐问题的论析为主线,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可以置之不理。相反,从专著写作的系统性要求出发,必须尽可能地面面俱到,但各个方面和问题又必须置于恰当的地位。对于目前流行的所谓信息流通主导活的制度史研究,似可商榷。应当承认信息流通的作用,有时军事情报和政治情报的准确和及时,甚至也起了极端重要作用。但只消作一点思考,在阶级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对信息的通塞和真伪,起主导作用者,正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例如,宋朝法律规定地方官有灾必报,但秦桧独相专权时,为了装饰所谓中兴盛世,知法犯法,反而要处分上报灾异的官员。比信息传递系统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信息传递的窒碍,又何以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虚报、瞒报之类?即使作了上述研究,至多也只能是活的制度史的一部份。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法治是法大于权,人治是权大于法。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法制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其基本状况正是统治阶级往往以私利粗暴地践踏自己制订的法制。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包括地方政治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依个人之见,本书对地方政治中的文书传递、架阁之类,作了必要的论述,却没有夸大,是恰当的。
目前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个重大不足,是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运用。贾芳芳先生能遵循已故河北大学漆侠先生的倡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就显得可贵。当然,从此部专著看来,此种学习和运用也才是开端,但持之以恒,必获更多的收益。